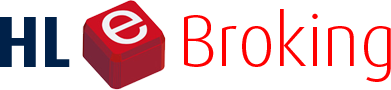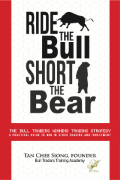增长已是过去式?/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Tan KW
Publish date: Mon, 16 Dec 2019, 09:39 AM
情况很明显:我们的生活所需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承载极限。除非我们做出某些改变,否则后果将极其严重。那么这个“某些”会是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关注吗?
气候变化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突出风险,而且我们已经对其所带来的成本略知一二了。在这个“我们”之内也涵盖了美国人。
作为国内其中一个主要政党由气候变化否定者所执掌的国家,美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全球最高,也是唯一一个拒绝遵守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国家。
而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也已成为洪水、火灾、飓风、干旱和严寒等极端天气事件相关财产损失最高的国家之一。
曾几何时,一些美国人甚至希望能从气候变化中受益。比如缅因州沿海水域将因气候变暖而吸引前来玩水的人。
即便今天仍有少数经济学家认为,只要我们能将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幅度限制在3至4°C(而巴黎协定将上限设定在2°C)就无需担心。这堪称一场愚蠢的赌博。温室气体浓度预计将达到数百万年来的最高水平,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豪赌就将无处可逃。
那些表明我们可以忍受更高温度的研究也存在严重缺陷。
例如,由于有组织地刻意忽略掉适当的风险分析,因此这些研究的模型未能给发生“不良结果”的可能性赋予充分的权重--对不良结果的风险赋予的权重越大,推导出来的后果就越糟糕,而我们也应当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
通过将很少(甚至过少)的权重分配给非常不利的结果,这些研究就会系统地偏向于那些不应采取任何措施的分析结论。
此外这些研究还低估了破坏函数中的非线性特性。
世界变得更贫穷
换句话说,我们的经济和生态系统可能对温度的微小变化具有弹性,破坏程度仅与温度变化成比例增加,可一旦气候变化达到一定阈值,破坏的增长就会相对于温度上升而加速。
例如,由于霜冻和干旱、农作物损失变得严重。低于阈值水平的气候变化可能不会影响发生霜冻或干旱的风险,而高于该水平则会不成比例地增加这些爆发极端事件的风险。
而我们才最无力去承担气候变化的成本之时,恰恰是当其后果变得巨大之时。没有保险基金可以拿钱出来让我们投资于应对海平面大幅上涨,不可预见的健康风险以及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大规模移民。
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世界将变得更加贫穷,消化这些损失的能力也将降低。
最后,那些主张对气候变化采取观望态度的人--即所谓今天采取大规模行动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风险是浪费金钱--通常都会以较高的折扣来评估这些未来的损失。
也就是说每当有人采取一项具有未来成本或收益的行动时,就必须评估这些未来成本或收益的现值。
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如果五十年后的一美元与今天的一美元一样值钱,可能会激励人们采取有力行动来止损。但是如果50年后的一美元只相当于现在的三美分,那么人们就不会采取行动。
因此折现率(我们如何评估相对于今天的未来成本和收益)就显得至关重要。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已经表示当前不想花费超过三美分来防止50年后的一美元损失。这对未来几代人来说算不了什么钱。
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那些无视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公共经济学所取得的所有进步--这些进步都说明了另一种做法的合理性--的不作为倡导者们则认为经济效率需要我们无所作为。他们错了。
我们现在必须采取强有力行动以避免世界堕入气候灾难。
而令人鼓舞之处在于有如此众多的欧洲领导人为确保全球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做出积极努力。
经济要高质量增长
我与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共同主持的碳价格高级别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也指出,可以通过一种可以提高生活水平的方式,实现巴黎协定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C以内的目标:利用向绿色经济的过渡来刺激创新和繁荣。
也正是这一观点,使我们不同于与那些认为只有通过停止经济扩张才能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人。我相信后者是错误的。
但无论人们对GDP不断增长的痴迷存在多少误导性,如果没有了经济增长,全球仍将有数十亿人继续陷于食物、住房、衣服,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匮乏当中。
而我们仍有足够的空间来改变增长的质量以显著降低其对环境的影响。比如即使未能实现重大技术进步,我们也可以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但是碳中和不会自发产生,将其留给市场也无法实现。只有将高水平的公共投资与强力法规和合理环境定价相结合才能达到目标。
而如果我们将调整的重担都放在穷人身上,这不可能也不会发生:须知环境的可持续性只有在努力实现更大社会公正的同时才能成为现实。
http://www.enanyang.my/news/20191214/增长已是过去式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