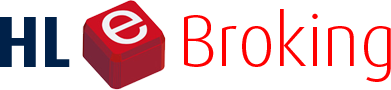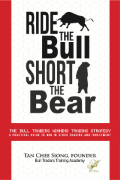今日危机有所不同/Project Syndicate
Tan KW
Publish date: Sun, 19 Jun 2022, 07:50 AM
就像一代人终究要让位给下一代人一样,新一代全球挑战也将取代原有全球挑战的位置。
百年一遇的2019年新冠疫情--以及其他危险新病毒随时可能浮出水面的风险--还远不是唯一的例子。
由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正在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信息技术和数据有时会被恶意利用,或者被用于网络战。
即便是今天飞涨的粮食价格和日趋严重的全球饥饿,也可以被归咎为未能实现开源技术的广泛传播。
我们似乎生活在永久的危险状态中。危机已不再是仅仅影响少部分人的孤立的尾部风险事件。它们更为频繁、多维且相互依存,而且--因为它们能跨越国家边界--因此,有可能同时影响所有人。
此外,它们牵扯到如此之多的外部因素,以至于市场和国家政府都没有足够的动力来解决它们。
能否解决上述问题,取决于能否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但目前所运行的国际体系却无法足量提供。
例如,我们必须在疫情防范和应对、抑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共同弊端)领域进行大规模统一投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仅凭一己之力解决当前的危机,更不用说预防新危机的爆发。
重新思考多边主义
重新思考多边主义的运作方式势在必行。战后国际金融架构旨在支持国家政府,以便它们可以提供国家公共产品。但构思能跨越国家边境提供公共产品的新机构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当前危机的相互重叠性,为建立全新框架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理由。洪水和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加大了爆发传染性疾病和水传播疾病的风险。
平均气温升高以及降雨模式,改变正在降低对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主粮作物的潜在产量(例如,玉米产量下降了6%)--而对身体健康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粮食安全。
2010-2019年,全球陆地表面在任意月份遭受极端旱灾的比例高达22%,高于1950-1999年期间的13%。
2008-2009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上述危机实际是一种发达国家现象),抑或1990年代末的亚洲和拉美金融危机等,此前的突发事件其本质上均具有经济属性,究其原因是由于金融风险的过度累积。
当时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手中掌握着解决方案。他们引入了全新金融法规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旨在恢复失去的就业和产出。

当前的粮食危机应当触发应对此类威胁所需的全球合作。
全球化危机依存
相反,当今危机相互依存且在范围上真正具有全球性,因此,可能造成的影响比以前大得多。不同的是,解决方法不再完全取决于国家经济当局的能力。
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世界各国政府积极领导并采取行动。拟成立的全球健康威胁委员会,是这种方法的实例。
早期发现疫情威胁和研发针对已知病原体的群体免疫,即是非竞争性及非排他性全球公共产品的典型案例。
但个别国家纳税人缺少动力,提供能使全球受益的公共产品。此外,我们也不能指望官方发展援助(ODA)或慈善团体来完成这项任务。原有的援助金额根本就与需求不符。
去年官方发展援助总额达到1800亿美元(约7920亿令吉),而私人捐助机构则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额外援助。但全球公共产品需求则需要数万亿美元才能满足。
此外,援助预算太过周期性,而且其首要任务也是不断变化的。但看似紧迫且具有政治吸引力的事务并不总能与重要的事务相一致,而后者才应当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点关注。
这解释了我们为什么需要引入全新多边体系的理由。理想状况下,该体系的主要因素应当反映提供国家公共产品所需的工具:包括税收、激励措施和问责制度。
建设全球财政能力
由于全球公共产品需要巨额稳定融资,所以,我们应当重点关注建设全球财政能力,并以支付能力为基础提供统一资助。当然,同时还需要国家层面的领导,以确保跨政府和跨部门采取充分的对策。
正确激励纳税人及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并非易事。但绝大多数政府均对国际货币基金(IMF)依据第4条规则所定期举行的磋商持重视态度;评估它们如何应对气候及疫情风险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同样,信用评级机构应当拓展其赖以评估政府和企业风险的方法。
世界并未做好准备应对新一代危机。当危机来袭时,与其仅仅关注某特定领域的不足之处,我们更需要了解,我们为什么完全不擅长提供应对上述全新危机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
除非我们能解决上述问题,否则特定问题将不断出现。例如,如果明天就将爆发又一次疫情危机,那么我们或许不会比2019年新冠疫情应对得更好。
当前的气候、卫生和粮食危机应当触发应对此类威胁所需的全球合作。如果它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必须询问什么才能做到。
Project Syndicate版权所有
https://www.enanyang.my/名家专栏/今日危机有所不同project-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