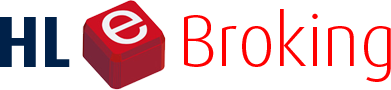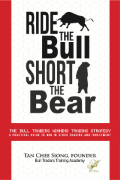IMF不懂资本管制/Project Syndicate
Tan KW
Publish date: Sat, 28 May 2022, 11:03 PM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IMF)执行董事会上月批准的管理跨境资金流动政策,修订框架扩大了各国限制资本流入的应用场景,却也不幸地过度束缚了它们的手脚,且未能考虑到它提供的建议究竟能否适应无数现实情况。
因此,尽管反复无常的资本流动已经对许多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构成了持续挑战,新框架却只会减少各国实现其社会目标的选项,并可能最终导致全球经济变得更加不稳定。
之前那个2012年获批的IMF框架--被称为“机构观点”-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处于危机时控制资本外流才具有合法性,而对资本流入的管制也只应在国家经历外国资金激增时作为最后手段使用。
这个机构观点其实是一个政治妥协,反映了一些赞成资本流动完全自由化的IMF成员(包括一些大股东)与那些希望IMF出手采取政策缓解波动的国家(涵盖许多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深刻分歧。
“管得太宽了”
一些国家反对机构观点并不是因为不同意它,而是觉得它“管得太宽了”。
它们担心IMF正在超越其章程(协定条款)规定的职权范围,该章程在资本控制政策方面给予了各国相当大的自由度,同时容许未来的IMF董事会突然改变政策方向并试图限制各国的行动范围。
不能“以邻为壑”
IMF的职责是防止各国政策产生负面国际溢出效应。
基金的创始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亨利·德克斯特·怀特,对竞争性货币贬值的影响深感忧虑,因此在基金多项条款中强化了反对“以邻为壑”政策的规则。
而我们最近也见证过某一国金融问题蔓延到他国时可能发生的状况--正如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那样。
当年制定IMF协定条款的时候,大多数国家--包括当今这些发达经济体--都在广泛实施资本控制,因此这些条款并未赋予基金组织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权力。
此外,最后一次延长条款的尝试--IMF 1997年香港年会--踩在了一个最糟糕的时点上:当时刚好爆发了由大量资本外流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
一般来说,那些货币未被低估的小国既不产生负外部性,也不会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
因此它们采取的资本管制,通常不会与IMF的职权范围发生重合。
许多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会限制外国购买房地产来确保本国中产阶级买得起房子,这些限制就不属于IMF的职权范围,尤其是在这些措施不会导致汇率大幅贬值,或催生重大跨境金融溢出效应的情况下。

IMF最近敦促澳洲重新考虑对流入塔斯马尼亚的房地产资金征税。
监督可信度受损
然而,IMF最近却敦促澳洲重新考虑对流入该国塔斯马尼亚州(只有54万1000人口)的房地产资金征收小额税金的措施(尽管该措施不可能具有宏观经济意义)--这只是众多例子中比较明显的一个。这类建议以及涉及加拿大和新加坡等不同国家的相关立场,都破坏了IMF“监督”(监测)行为的可信度。
IMF的修订框架明智地允许各国在某些情况下,提前对资金流入采取措施。该基金已经认识到等到金融失衡达到临界点时才采取行动是不明智的。这一本质上针对预先宏观审慎监管的基本原理既适用于因国外热钱产生的失衡,也适用于国内过度借贷引发的失衡。
那么在外流这一侧呢?鉴于美联储当前正在提高利率,这个问题对许多新兴市场来说至关重要,然而IMF的新框架却奇怪地回避了这一点。
经济学家普遍会对资金流出管制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担心这种政策会不可避免地等同于部分征用。但这其实与政策设计以及游戏规则是否明确并提前告知有关,比如事先出台一些对短期资本外流(但不包括长期资本流动)征税的政策,并在危机发生时实施更广泛管制的做法,其实可以最终巩固宏观经济稳定并因此吸引更多外国投资。
而评估是否需要外流管制、如何改进其设计以及它们在国内可能发挥的作用,则是IMF工作的一部分。
传统智慧不断演变
传统智慧也在经济理论的进步下不断演变,而这也清楚展现了在某些情况下,实施资本控制的谨慎性特质。
1990年代末(IMF倡导全面资本账户自由化)的禁忌与2012年(赞同在资本激增时实施流入管制)和2022年(赞同预先流入管制)的禁忌是有所不同的。
而就连IMF都明白,或许资本外流管制作为其对阿根廷前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执政期间贷款的一部分措施是可取的。
如果没有这项管制,那就等同于IMF放任国际投资者将他们的钱撤出该国,只留下阿根廷背负440亿美元债务且毫无建树。
在阿根廷面临的这种情况下,IMF应考虑的不仅仅是允许对资本外流进行管制,而是要切实坚定地管制。
IMF的协定条款正确地给予了成员国政府实施资本管制的广泛自由,只要这些政策不会以邻为壑地损害其他国家就行。
富国已经充分地利用了这种灵活性。而IMF能做的莫过于继续秉承其创始人的精神。
Project Syndicate版权所有
https://www.enanyang.my/名家专栏/imf不懂资本管制project-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