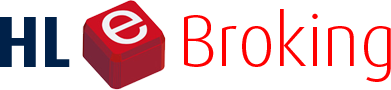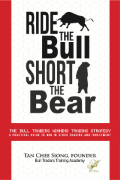“安华经济学”的挑战/黄锦荣
Tan KW
Publish date: Tue, 29 Nov 2022, 09:03 AM
安华还是副首相的时候,新自由主义兴起,那可是一个市场机制挂帅的年代,主张跨境贸易和金融市场自由化,是累积财富的唯一途径,并认为所有人将受惠于经济增长。
虽然亚洲区经济普遍蓬勃的发展,确实少不了贸易自由化的功劳,中国经济入世贸以后的崛起,更是佐证了开放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改革,但经济增长却不必然惠及所有人,成长果实也不全然下渗到基层人民。
市场开放固然可催化更有竞争力的商家,生产更有附加价值的商品,创造更高薪的就业机会,但不是所有行业都能参与出口市场,更多的是被进口碾平,否则作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我国出口量又怎会仅由那1%的大企业和1%的中小型企业所主导?
自独立以来,我国就不曾停止过招商引资,如果外资的投入要真的能解决低薪的问题,我国那近乎500万受薪族的每月工资,就不会在2021年也仅是2250令吉或更低。
再说,我国去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万7439令吉,或月均3953令吉,与2250令吉这中间工资相比较,工人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就很明显,因为酬劳仅是所创造的附加价值的57%而已。

物质存在决定意识
安华当年就曾经提过,大学经济课所传授的不该只限于主流思潮,应该也包括非主流思想,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然,没有人想要提倡无产经济,因为无产社会是经济运转失序败坏的根源;也没有人要主张无神论,因为如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所论,始于18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经济学,离不开基督新教的影响。
但安华要是翻阅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应该就会涉略过,经济基础的矛盾是政治这上层建筑发生变更的导因,而不是那些政治的、宗教的意识起了冲突,即便是意识冲突也必须从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矛盾去解释。
换句话说,人们的物质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回到第十五届大选的结果,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半数以上的马来票都投给了国盟,而大部分也都来自于处在经济发展边缘的北马和东海岸。
如此显著的族群和城乡地域的分野,难免会引起众人忧心,团结政府是否会走回头路,从宗教的视角来回应政治版图的变更,一如当年马哈迪和安华联手伊斯兰化政教,以抵御回教党影响力的扩张。
回溯既往,团结政府想必明白,就伊斯兰化来说,没有任何政党可媲比以伊斯兰化为唯一目的的伊党。但伊党的伊斯兰议程,不是伊斯兰化的唯一选择。
如果团结政府在往后的日子,尝试推出伊斯兰化的替代诠释,切记这一次的选票分布,并不意味着马来群体是铁了心,一心一意地追求精神世界而不再在乎世俗的物质条件,因为其中还掺杂着对巫统的失望,和对希盟能否保护马来族群经济权益的怀疑。
百姓福利为目的
所以,安华任相后最大的经济挑战,就是从过往误认招商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等手段为目的,以为老百姓自然而然地会受惠的发展模式,过渡到以老百姓福利权益为目的,招商引资及经济增长为手段的经济模式。
套用老马(唉!我指的是马克思)的语境,就是通过扩大经济基础来巩固政治上层建筑,而所谓的经济基础,指的不是仅涉及少数政工商精英的招商引资、开发经济增长新源头等经济活动,而是托克维尔观察中的市民社会,一个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生活,一个涉及大部分老百姓的生产与分配关系。
一旦改变老百姓的生活素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板块再厚,也有被移动的可能。
https://www.enanyang.my/名家专栏/“安华经济学”的挑战黄锦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