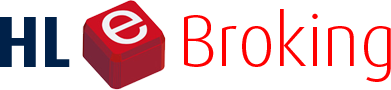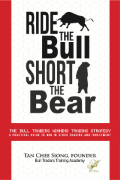省思大马经济增长两拐点/黄锦荣
Tan KW
Publish date: Tue, 06 Feb 2024, 10:33 AM
大马经济增长有两个重要的拐点,一是在1985/86年,另一个则是1998年。
在1961年至1984年期间,平均实际经济增长率是7.3%,标准差是2.3%,变异系数为0.3,所以那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年代。
但由于经济结构依然过度依赖自然产品、农业等第一产业,而工业发展仍在发展初期,产业多以加工处理天然资源为主,深被原产品价格周期所牵制,所以增长率的波动颇大。
1985年,令吉因日元急剧升值而贬,引爆公共债务危机。那一年,我国经济自独立以后第一次陷入衰退,负增长1%。虽然萎缩程度比起我国日后所经历过的衰退,是小巫见大巫,但隔年经济反弹迟缓,仅仅增长了1.2%,整体经济都“弥漫着悲观向下的情绪”。
法德英美日在1985年达至的广场协议,是导致日元急升的主因。同样的协议,也开启了以日本为主导的区域制造供应链。
在关税壁垒逐渐瓦解、网际网络及通信科技蓬勃兴起、冷战结束后各国高举贸易全球化旗帜的大环境下,大马也融入全球生产价值链当中,制造业顺理成章地成了经济主干。
金融危机掀千层浪
直到亚洲金融海啸掀起千层浪以前的那十年里,大马实际经济平均年增9.3%,八年里经济规模就翻了一倍,而且波动性极低,标准差仅是0.76%,变异系数更是0.08之低。
追根究底,那是投资驱动使然。金融资本随着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大量涌入,催化了非贸易类投资,而全球生产链形成下所产生的跨境贸易也带动贸易类投资。
在商业及金融投资驱动下,经济增长于是乎得以平稳地快速发展,缩小与前沿经济体的鸿沟。
亚洲金融危机却是大马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拐弯点。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那一年,十年平均增长率就突然降了一个水平,从9.3%掉到了5.6%。
疫情未改结构
大衰退对大马经济的冲击并不大,2019年经济仅陷入小幅萎缩,隔年增长率也强劲反弹,即便如此,随后至疫情爆发以前的另一个十年里,年均增长率却还是微降至5.4%。
至于疫情衰退以后的经济增长表现,也不见结构性改变的踪迹,过往三年的年均增长率甚至是进一步下掉至5.2%。

吸取哪些教训?
回看过往六十年的经济增长,我们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经济高速增长的1988-1997年,关键是投资驱动,但事过境迁,如今大马经济规模是1997年的三倍之大,资本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难以复当年之勇,更何况全球生产价值链早有掉头趋势,跨国金融与商品贸易更参杂了国家安全考量,我们很难再透过产业链的参与来复制当年的增长奇迹。
至于增长率突然降级的那二十年里,我们从不缺外来直接投资,也不曾间断开拓新增长领域。
这些努力固然可以深化我国产业的复杂性,但显而易见的是,它对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任何质的变化。
1997年,我国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15%,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那比例却停留在18%,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我在给学生准备有关于长期经济增长的讲义的时候,重温了哈佛大学的菲利普·阿吉翁及布朗大学的彼得·霍伊特于2006年的一篇旧作,文中谈及了技术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来自于实施创新和前沿创新的此消彼长。
我国经济发展,一路走来,基本上已具备实施创新的技术能力。但经济发展越是靠前,门槛低的实施创新,对于经济增长而言,越是不重要。
迎来第三拐点?
经济增长届时是否能取得质的跃升,那就得看看前沿创新的技术底蕴垫得厚不厚实,否则就只能望着脱离中等收入陷阱的门兴叹。
然而,以我国每年的专利申请不过千、科研开销仅是GDP的1%的形势来判断,经济增长能否迎来另一个拐点,还真的不好说。
https://www.enanyang.my/名家专栏/省思大马经济增长两拐点黄锦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