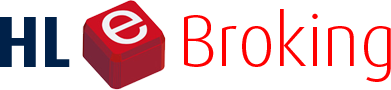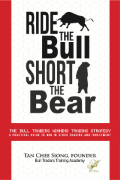中国经济改革缺创新/Project Syndicate
Tan KW
Publish date: Tue, 06 Feb 2024, 10:34 AM

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其容易通货紧缩的债务密集型经济表现严重不佳。其政府卷入了与美国的重大超级大国冲突。其面临着人口危机。
最糟糕的是,中国当局更多地用过去的意识形态和陈旧的策略来应对这些挑战,而不是通过突破性的改革。解决棘手问题的富有想象力的方案供不应求。
在过去2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一个顽固的中国乐观主义者,我从未轻易得出这个结论。我在耶鲁大学开设的课程“下一个中国”(The Next China)提出了一个中国增长模式的有力转变,即从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国内消费驱动型经济。
从乐观到怀疑
是的,我担心中国千疮百孔的社会安全网--无论是退休还是医疗--可能会导致恐惧驱动的预防性储蓄增加,从而抑制消费者需求。但是,我认为这些担忧更多的是挑战而不是风险,我仍然相信中国最终会实现经济再平衡。
2021年,我开始产生严重的怀疑,当时中国监管机构对互联网平台公司进行了打击。企业家遭到致命打击,我警告“动物精神赤字”正在增加。在我的新书《意外冲突》(Accidental Conflict)中,我扩大了我的担忧范围,纳入了习近平主席的“共同富裕”运动的影响,它将目标对准了中国冒险者的财富创造。
接着,在一年前我认输了;在《一个中国乐观主义者的哀叹》(A China Optimist's Lament)一书中,我指出政府对国家安全的新关注将进一步削弱中国的经济活力潜力。
我的看法的改变遭到了相当多的抨击,尤其是来自长期持有偏见的美国政客及其媒体伙伴的抨击。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对辩论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尤其是关于下一个中国开始看起来更像下一个日本的可能性的问题。
在过去几个月的一系列的对华访问中,我与众多高级官员、商界领袖、学者、以前的学生和朋友讨论了这些问题,我得出三个结论:
三个结论
首先,中国对经济萎靡不振的政策反应并不明智。政府依靠长期以来所谓的“积极的财政刺激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支持,展望2024年经济增长5%左右(李强总理将于3月在全国人大上正式宣布这一目标)。与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况一样,中国再次诉诸大量注入现金的蛮力,以解决当今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股票市场的重大混乱。
其次,这种短期的反周期策略并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的长期结构性问题。据联合国估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达到顶峰,到2049年将减少近2.2亿。基础经济学告诉我们,要用更少的工人保持稳定的GDP增长,就需要从每个人身上榨取更多的附加值,这意味着生产率增长至关重要。
但是,随着中国现在从低生产率的国有企业那里获得更多支持,以及生产率较高的民营部门仍然面临巨大的监管压力,生产率加速增长的前景看上去十分黯淡。
最后,政府不断加强对内部安全的关注。最近针对军方的反腐措施,以及对民营部门的反复的监管攻击,都是如此。例如,游戏行业再次受到审查,几位备受瞩目的外国高管也是如此。
此外,刚刚闭幕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中全会强调了思想纪律作为基本价值的重要性。
为此,共产党实际上接管了中国一些领先的教育机构,包括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和福州大学。

克鲁曼
生产率引担忧
我最担心的是中国的生产率,尤其是老龄化对劳动率构成的影响。生产率对中国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同样重要。
学者们关注生产率增长的几个主要来源--技术、人力资本投资、研发以及国民产出组合的行业间变化。已故的现代增长理论的发明者罗伯特·索洛说得最好,他将生产率界定为在考虑了劳动和资本对产出的物理贡献之后的技术进步的“剩余”值。
保罗·克鲁曼在1994年《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中,将索洛增长核算框架带入了经济发展的思考。
克鲁曼认为,被捧上天的东亚四小龙快速增长表现反映了通过建设新产能、让低生产率农村地区的工人前往高生产率较的城市而实现的“赶超”增长。
克鲁曼在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先见之明的警告中强调,这些经济体最终未能贯彻索洛生产率剩余中蕴含的启发性天才--或者可称之为缺乏想象力。
我最近三次访问中国,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中国领导层正遭受着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想象力不足的困扰。他们根深蒂固的反周期政策思维与日益加剧的通货紧缩风险格格不入,而人口迅速老龄化和严重的生产率问题之间的致命相互作用进一步加剧了问题。与此同时,政府正在通过一连串法规扼杀创新,试图从意识形态中汲取灵感。
如果没有更具想象力的经济管理方法,中国可能会陷入困境,无法鼓起改革者过去如此成功的勇气。
Project Syndicate版权所有
https://www.enanyang.my/名家专栏/中国经济改革缺创新project-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