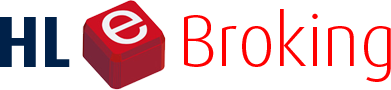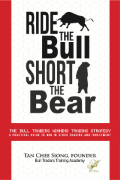诺奖和最低薪金制/黄锦荣
Tan KW
Publish date: Tue, 19 Oct 2021, 08:21 AM
犹记得我们在2013年1月正式实行全国性最低薪金制以前,坊间争论激烈。
赞同的那一方认为,为员工的薪金垫个底,那是给予劳力付出者一个基本的尊重,因为于2012年近乎一半的家庭的人均月收入是少过982令吉的。
反对的声音,则多从营运成本的角度发出,以为那会导致企业不胜负荷高昂的劳动力成本,进而裁员,结果最低薪金制是好心做坏事,为薪金铺底不成,反而丢了垫。
孰是孰非,当时没人说得准,即便是经济学者之间的立场也分东西。
但最低薪金制能重新出现在公共政策的主要菜单里,那可要追溯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维卡德(David Card)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在1994年发布的一篇开拓性的科研文章,探讨的就是最低薪金制对就业所带来的影响。
当时美国的新泽西在1992年通过了最低薪金法,但宾夕法尼亚州却没有。由于两个毗邻的社区仅隔了一条河,经济结构和商业循环非常相似,因此劳动市场的变动大致上同步。
但因为出现了最低薪金制的不同调,于是乎,一个随机形成的对照环境出现了,即经济学者所谓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让两个地区之间的就业机会差异,得以反映最低薪金制的影响。
卡德和克鲁格发现,最低薪金不但不会伤害就业机会,对就业机会的增长反倒有些积极的贡献。
此文一登,争议不断,因为此发现有违当时学界的普遍认知,以为薪金既然完全反映了员工的生产力,低酬劳就意谓着低生产力,你不去搞好生产力,反其道而行来设定最低薪金,那不就是等同于给商家添麻烦,就业机会怎么可能不减反增?那一定是伪科学了。
但卡德和克鲁格一文终究还是开启了自然实验在经济实证研究的天下,为依证政策制定(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开疆辟土,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实证累积,经济学界来到今天,对于最低薪金制也多持肯定的态度。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上周一,更是把2021年二分之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卡德,以表扬他于劳动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巨大贡献。
回看大马数据,虽然直接受最低薪金制影响的就业空缺增长在2013年1月以后下滑,但是缩减的幅度比整体就业空缺的萎缩来得小。
应依证制定政策
更有趣的是,当最低薪金在2016年7月上调至1000令吉以后,低薪就业空缺增长的速度,比整体就业空缺的还要快。这似乎也意谓着低薪就业机会随着最低薪金的落实不减反增。
我想主因是劳动市场摩擦很多,员工的流动性并没有想象中的顺畅。
由于切换工作对于一般员工而言耗时费力,既有家庭和地理环境的限制,也有薪金以外的考量,员工和雇主在薪金上的议价能力一开始就向后者倾斜,薪金因此都是要低于劳动生产力的。
通过最低薪金制把薪金往上一推,那只会把雇主额外所得的份额,重新分配于低薪员工,却不会削减整体营收表现,对于就业空缺也因此没有负面效果。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全国统一执行的政策,我们无法百分百鉴定最低薪金是否导致企业裁员或者减少聘请,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自然对照环境来分辨那些置身于最低薪金制地区的企业的表现,是否有别于不受最低薪金牵制的企业。
我国的决策圈实在是有必要和学术界认真地建立起依证制定政策的传统,要不然纯粹依偏好拟策,我们也就仅能走这么远。
https://www.enanyang.my/名家专栏/诺奖和最低薪金制黄锦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