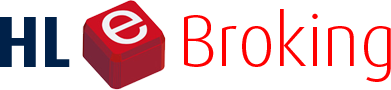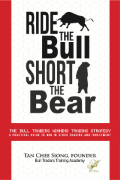输入外劳输出马劳怪象/胡逸山博士
Tan KW
Publish date: Fri, 14 Jul 2023, 09:31 AM
本地也还算是很幸福、很“好命”的。因为许多如本地般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长期低迷,许多民众难以找到生计,所以是大量的输出彼等的劳动群众到经济状况更好的外国去当外劳打工,以赚取外汇寄回家乡养活家小。
笔者还记得首度到菲律宾去公干时,看到首都马尼拉的机场,竟然有着为所谓的“菲律宾海外工作人员”所设的特别通道,彼等人数的庞大可想而之。而菲国以及笔者也到访过的孟加拉,也都有为各自管理输出外劳的官方部门。
另一方面,在中东的许多富裕国度,大家看到从最底层的厌恶性行业,一直到高档的服务业,多由外国工作人员所操作。而在个别较小的中东国家里,这些外劳人数竟然超越了本地人口数倍之多,可见彼等的社会经济运作对于外劳的依赖性。
而本地在这方面其实也不落人后,赫然从至少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输入许多的外劳。譬如说当下已然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其实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也还算是个发展中国家,也免不了需要输出外劳。
有发达国家现象?
在笔者生长的东马沙巴,在那个时代因为伐木业的兴旺,也还颇为富裕。笔者小时就看过韩国的劳工在首府亚庇的建筑工地里辛勤工作。后来彼等之中有一部份也留下在沙巴,为本地社群增添了更大程度的多元色彩。
后来沙巴也有越来越多来自印尼东部摩鹿加群岛以及帝汶等的劳工,在园丘以及本地人家庭里工作。
在西马,建筑工人好像多来自孟加拉、缅甸、印尼等。工厂工人与家务助理,则好像多来自印尼中西部爪哇、苏门答腊等,彼等在本地的工作待遇与生活福利等,也常成为本地与印尼之间的双边关系的一个主要摩擦面。
而在如餐饮、零售等行业,本地也如新加坡、中东各国等,出现了越来越多来自菲律宾与孟加拉的服务员,说着口音浓厚但又流利的英语。所以从这些大幅度依靠劳动的角度来看,本地俨然已经很像那些发达国家了。
然而,假如我们有到访其中一些发达国家的话,却也可能看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当地社会劳动现象。
一方面,譬如在日本、韩国、澳洲等,鲜少会有外国劳工在工地、工厂、家庭、服务业等干活,绝大多数都是由当地的工人在这些行业里工作。

每逢公共假期,吉隆坡就会变成“外劳城”。
是时候结构性改革
在当地就算有所谓的“外劳”,其实也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意义里的“外劳”,即彼等很少是大规模、系统性地被从外国输入到当地去工作,而多是当地的新移民们基于从低做起的社会流动原则,个别、零星地去从事这些行业。
另一方面,我们却也看到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柔佛同胞当日来回过长堤到新加坡去工作,以赚取汇率相比于本地很高的新币。在一些中东国家,据说也有越来越多的“马劳”。
本地这种相对畸形的劳动市场现象,一方面输入大量外劳,另一方面自身的劳动人口却也流失,常远来说,是会弊多于利的。
以上日、韩、澳等的例子阐明,多用本地劳动力而少用外劳是可能的,无非就是加强技职教育、合理化薪资水平、改变社会与商界的态度。是时候集思广益地来结构性处理这本地劳动怪象了。
https://www.enanyang.my/名家专栏/输入外劳输出马劳怪象胡逸山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