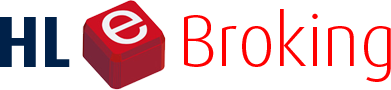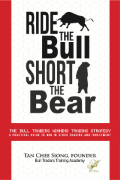国行货币政策近局限/黄锦荣
Tan KW
Publish date: Mon, 05 Apr 2021, 11:47 PM
货币政策多年来都是稳定宏观经济最重要的调控工具。之所以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其中之一”,那是因为货币政策的执行,远比财政支出和税减直接而干脆,代价也小得多。
举个例,经济动力要是滑落,显露衰退迹象,财政部固然可以宣布减税或者增加基建和福利开支,但是减免的税项,那可是到了隔年缴税期方才见效,而基建建设的拨款不仅耗时,能否全数到位也还是个问号,至于福利开销则不是人人皆得,更何况政府举债花了的钱,他日还是得通过增税和减缩开支来偿还的,羊毛终究出在羊身上。
相比之下,国行的减息应对就有立竿见影之效,通过多方传导机制来振兴经济。
无需赎回已发货币
商家和个人的银行借贷成本不仅随即减轻,上市公司股票的估值也因折现值提高而更具吸引力,一推一拉地促使存款人抓紧投资房股市的时机,随之出现的财富效应配合利息的下降,进一步推动对耐用品的消费,而令吉也因降息而趋软,增加出口所得。
重要的是,国行并不需要赎回已发的货币,政策代价近乎零。
然而,国行的传统利息政策,似乎是越来越靠近它的局限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那一年,平均隔夜银行同业拆息为7.6%。为了应对经济衰退,银行同业拆息于1999年下降至3.4%,随后持续降至最低的2.7%。这一轮近乎500个基点的降息循环维持了将近7年,直到2005年11月。
国行再次降息时就是全球大衰退那一年,当时的隔夜政策利息为3.5%,国行在2008年11月开始降息,于四个月内减了150个基点至2%。不过那一次的降息循环仅维持了13个月,并在2010年3月开始升息。
值得留意的是,升息循环于2011年5月上调了100个基点至3%以后就上不去了。期间国行虽然尝试再上调25个基点,没多久又回降至3%,直到疫情爆发。

改变手段势在必行
政策利息上调不了,这和摸不着、看不见的自然利率有关。
如果公共和私企的总体投资疲弱,对资金需求不足,又或者生产力增长缓慢,自然利率就会偏低,政策利息上调空间就会受限。
政策利息要是乖离了自然利率,借贷成本就会偏高,进一步打击资金需求和生产力,经济是要付出代价的。
政策利息要是在升息循环中上不了多少,那么在下一轮的降息循环中自然也降不了多少。
从亚洲金融危机时的500个基点,到全球大衰退时的150个基点,再到疫情期间的125个基点,经济发展的局限,限制了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进一步把传统利息政策推向零下界局限(意即利息的最低水平仅能是零)。
换言之,除非公共部门和私企在未来的十年内积极拓展研发和大举投资,并推高生产力增长,要不然国行要结束1.75%的低息循环的能力必定受阻,能上调的空间也将少于100个基点。
最致命的是当下一波经济衰退浪潮来袭的时候,国行降息稳经济的调控空间也将严重受限,没了法宝,神仙也难救经济。
所以国行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开始着手增设法宝,改变执行货币政策的手段,以催化私企的无形资产投资是其一,推动国行的数字货币以突破货币政策的零下界约束是其二,至于过程如何,我们下期再叙。
https://www.enanyang.my/名家专栏/国行货币政策近局限黄锦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