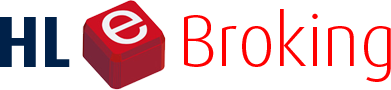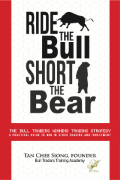助非洲做好应对冠病准备/阿道拉·欧考利
Tan KW
Publish date: Wed, 11 Mar 2020, 11:17 AM
六年前,伊波拉病毒蹂躏西非。伊波拉是一种高传染性致命病毒,但如果国际社会能够毫不迟疑地提供所需的支持的话,疫情的经济和人道成本原本可以低得多。
在面临迅速传播的2019冠状病毒病(前称“新冠肺炎”)时,政府和国际机构有可能犯下同样的错误。
伊波拉病毒在2014年7月到达尼日利亚,一位被传染的利比里亚男子飞抵拉各斯,当时我是当地一名医生。他来我的医院就诊时,我们完全没有准备。事实上,我和我的几位同事也被感染。
但至少这是一家私立医院,拥有相当多资源,包括流动水原和医用手套。此外,当我们怀疑我们染上了伊波拉时,我们的医务主管懂得立即联系州卫生部门和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州和联邦卫生部门立即开始动员资源。
最终,尼日利亚的伊波拉疫情在93天后得到了控制。八人死亡,包括一些我关系密切的同事。我幸运地活了下来。但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疫情要糟糕得多。
由于卫生体系孱弱,资源不足,这些国家急需国际支持以遏制疫情。但当支持最终到来时,总体而言已经太少并且太迟了。
2014年4月至10月间,联合国通过中央紧急响应基金(CERF)动员了1500万美元(约6300万令吉)。但到2014年8月,遏制疫情的预计成本高达7100万美元(约2.98亿令吉)以上。一个月后仅仅一周就有700例新病例,成本增加到了10亿美元(约42亿令吉)。
在缺少足够资金的情况下,医院的病床和隔离治疗单元不够,无法收治所有受害者。伊波拉受害者的亲属别无选择,只能违抗政府命令,将仍有传染性的病殁尸体弃置街头。
推迟拨款致疫情恶化
最后,在2014年9月,联合国制定伊波拉紧急响应任务(UNMEER)扩大医护措施,为响应者建立“共同目标”。到12月,捐赠国和组织承诺28.9亿美元(约121.38亿令吉)资金。但即使是这些慷慨的承诺,也无法很好地按计划兑现:到2015年2月,只有10亿多美元落实到位。
如此差距并不令人惊奇。据乐施会(Oxfam)数据,捐赠人的恢复资助承诺平均只能兑现47%,即使是这一数字也可能高估了受助国所得到的数字。这表明问责严重失位。当承诺无法兑现时,负责筹款的联合国机构不会通知公众。
这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拨款的推迟导致疫情恶化,从而增加总成本。当伊波拉最终得到遏制时,已经过去了三年,各国花费五倍于2014年9月的预计数字。近1万2000人死亡。
须设紧急纾困基金
历史似乎在冠病身上重演,但规模更大。已有疫情的国家包含了全球总人口的一大半。一旦疫情到达卫生体系较弱的非洲国家,特别是人口稠密的城市,新感染人数可能激增。
认识到这一风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已要求拨款6.75亿美元(约28.35亿令吉)为不堪一击的卫生系统做好从现在到4月的应对冠病的准备。
但是,到2月底,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是唯一响应这一要求的组织,提供了1亿美元(约4.2亿令吉)捐款。按此速度,到援助姗姗来迟时,非洲和其他地区将有不计其数的受害者。
2014-16年间的伊波拉疫情突显出全球危机响应的两个事实:紧急情况期间的筹资极少能够起作用,以及指责涵盖从飓风到干旱的CERF不足以独力担当。
因此,必须专门成立紧急纾困基金应对疾病爆发,并由捐赠过、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源源不断提供资金。
这不是慈善,而是自我保护。病毒不会尊重国家边境。我以为身在尼日利亚的我不会染上伊波拉,然后我就“中招”了。当意大利北部听说武汉爆发冠病疫情时,大部分人想必也不会想到会经历封城。
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可能能够对冠病传播采取强力有效的应对,但许多国家不能。当病毒传播到无力遏制它的社区时,有能力的社区也很快就会力有不逮。简言之,要么人人安全,要么人人不安全。
病毒的传播比政府和国际筹资人的动作更快。因此,我们实现疫情风险最小化的最佳机会在于确保足够的紧急情况纾困资金随时就位,在疫情爆发后立即分发。
如果伊波拉还没有教会我们这一教训,那么冠病肯定会。
https://www.enanyang.my/news/20200311/助非洲做好应对冠病准备阿道拉·欧考利/